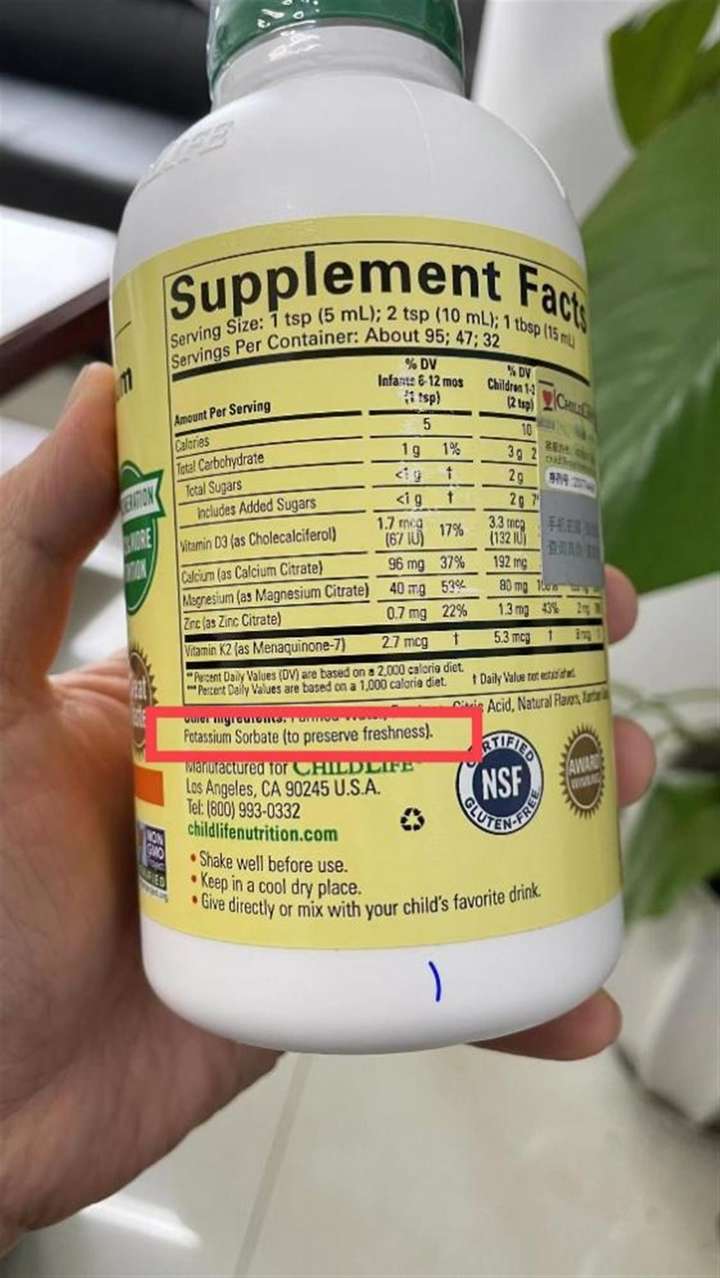(相关资料图)
(相关资料图)
胡仄佳是四川美术学院七八级毕业生,读的是油画专业。但我在本世纪初认识她时,却并不见她画油画,其注意力集中在写作和摄影上面,出了好几本散文集,配有自己拍的彩照,甚为灿烂夺目,令我非常羡慕。因为我也写散文,却不擅长摄影,出书时配的都是现成照片,虽然有一定的历史意味,但从审美的眼光视之,却并不好看。与仄佳慢慢熟悉之后,我才知道,重头戏还在后面。她在美院毕业之后不久,曾因偶然的机缘,来到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苗区,被那里的苗绣深深地吸引住,遂多次前往,从为数不多的工资中挤出钱来,收购绣片绣衣,持续十年。时间久了,也就有了相当的积累。她曾带着这批苗绣到澳大利亚做巡回展览,很受欢迎,这更引起她的珍视,遂想对这些艺术品加以深入的研究,写一本介绍施洞苗绣的著作。为此,她还特地去读了文科研究生,以提高自己的学术眼界和写作水平。但也许是因为太慎重其事的缘故吧,写书之事反而进展迟缓,当然还有其他杂事要做,一拖就拖了三十年之久。正应了那句老话:慢工出细活。
施洞苗老刺绣
现在仄佳终于将书写成,来信说要我作序。这大概是因为我对此书很重视,催促她写作甚力的缘故吧。我虽然知道这个题材的价值,但自己读的是文学专业,于美术和民族学均是门外汉,于苗绣本身也毫无研究,只是盛情难却,就来说几句门外的话,算是助兴。
刺绣艺术,并非苗族所独有,在全国各地都很常见,有些地区还相当出名,如苏绣、湘绣,就是苏州和湖南的产品。我的故乡浙江,因为盛产丝绸,是刺绣的上好材料,所以刺绣业也很发达。在那里,“刺绣”称为“绣花”,所绣以花草为多。当然,有时也会绣些其他东西,如动物、风景。那时,民间也常能见到绣品,但比较简单。绣花衣袄之类已很少见到了,大抵是在小孩子的帽上用平针绣一只虎头,以示勇猛,或绣上“长命富贵”等语以示吉祥,不似苗绣的针法多样,内容丰富。
从仄佳所介绍的绣件内容看,施洞苗绣不完全是一种装饰,更多是一种思想寄寓,因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所以,施洞苗绣的取材,远比汉人刺绣广泛,除了生活中所常见的动植物之外,还有从青铜器上描摹下来的龙纹、虎纹、鸟兽纹、云纹、雷纹等各种纹样,有人物图案,有清代咸丰年间领导苗民起义的男女民族英雄的绣像,还有据明宪宗朱见深所画《一团和气》图的变形画,甚至还有绣满汉字的盛装,当然,也有纯属民族传说的“蝴蝶妈妈”之类。民族学家将刺绣上的青铜器纹样,说成是远古时代蚩尤被黄帝战败后,逃到这里带来的器物图样。这是一种有趣的历史假说,但也只是假说而已,并无实证资料,远古之事,难言之矣。更大的可能,或许是与后来刺绣中的汉族图像一样,是苗民与中原人士的文化交流中带来的。
现代施洞苗刺绣的剪纸图样
因为施洞镇毕竟不是崇山峻岭,而是清水江边的一个码头。它是历史上向内地运送苗木的重要栈点,当然也会带回汉族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产品。而这些文化因素,就会渗透到施洞苗的刺绣中去。仄佳在书中饱含感情地抒写道:“当她们拿起针线进行刺绣时,祖宗遥远的呼声,清水江流船来船往,落花流水给她们带来灵动感受,她们的天地神人动物花卉是时间记忆与想象力的巧妙融合,我无法绕开这样的联想。”这个联想是有意义的。我们更可以从这遥远呼声和清水江流中,联想到施洞苗人的性格。他们既有民族的自尊,喜欢自己古老的传说,敬重敢于反抗入侵者的民族英雄,但也并非故步自封的闭塞山民,而有着吸纳他族文化能力的开拓者。在施洞苗绣中,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他民族的元素。
正是凭借着这条川流不息的清水江,在长年累月与外面世界的接触中,苗族文化在抗争和吸收中发展、壮大,施洞苗绣就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,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的研究。(本文为《“施洞苗”刺绣艺术图案探秘》序)
(吴中杰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