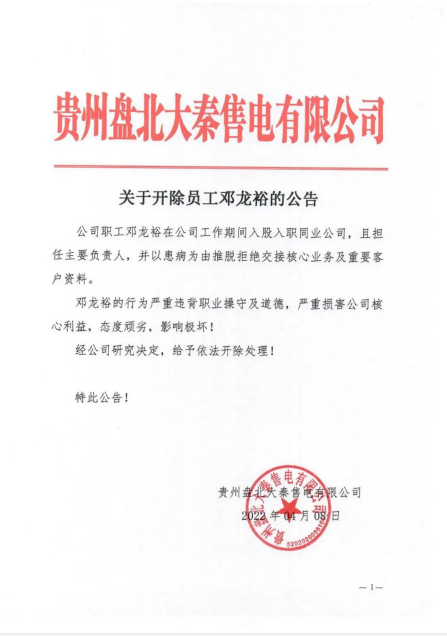一年四季,春夏秋冬,每个季节,大自然都会无私地馈赠给我们许多不同的美味佳肴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我住在农村老家。俗话说: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。”那个时候,老家的大山就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享用不尽的美味。
惊蛰过后,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,许多植物陆续从梦中醒来,睁开惺忪的睡眼,返青拔节,重新打量这个新的世界。春雨过后,老家后面的山坡上、土坎边、杂草中、土石旮旯里,到处都会悄悄地冒出一根一根的蕨菜,朝着我们一群放牛娃挤眉弄眼的,像在和我们嬉戏打闹,又像在和我们捉迷藏,惹得我们心花怒放。一到周末,我们就迫不及待三五成群地相约着去放牛,名为放牛,其实是拎着竹篮或背着书包在山坡上到处采蕨菜。
蕨菜,在我们老家又叫“蕨蕨菜”,是一种多年生落叶草本植物,喜欢生长于山坡向阳地带,春夏之交正是采摘的好时节。老家后面的山坡上随处可见,有的连片生长,有的独立成活。刚长出来的蕨菜叶片还未展开,探头探脑的,嫩嫩的、软软的,紧紧地蜷缩在一起,形状像婴儿的拳头,也像猫爪,像如意棒,所以在民间有的地方也叫做“拳头菜”“猫爪菜”“如意菜”。在阳光的照射下,蕨菜如雨后春笋般蹭蹭蹭地往上窜。它的茎秆呈黑褐色,很肥壮,有的有小手指一般粗,上面有许多细细的绒毛。蕨菜一般长到高出地面20厘米左右,是最适合采摘的时候。蕨菜长得很快,非常容易老,如果没有及时采摘,两三天后,它的叶片长出来就不能吃了。不过,从来没有采摘过蕨菜的要注意,山上有一种植物形状很像蕨菜,叫“里白”,是不能吃的,颜色比蕨菜稍白一点,我小时候就曾采错过。长成熟的蕨菜在我们这儿就不叫“蕨菜”了,叫“狼鸡叶”,茎秆很高,很硬,有的齐我们半腰,有的比我们放牛娃还高。它的根很粗但不复杂,一般在地底下横向生长,“狼鸡叶”的根可以加工制作成蕨根粉。在以前没有东西吃的时候,听说蕨菜和蕨菜根救了好多人的命。据说,蕨菜含有丰富的氨基酸,多种维生素,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,在餐桌上广受欢迎,制作方法多种多样,可以爆、炒、焖、凉拌或做汤,还能加工成干菜,腌制成罐头。我最喜欢凉拌蕨菜了。采来新鲜的蕨菜,清洗干净后,放锅里过一下滚水,再用凉水冷却,撕成条,切成段,放入葱花、姜粒、蒜末、芫荽、辣椒、水豆豉、酱油等佐料,搅拌均匀,红红绿绿,色香俱全,尝一口,黏黏的,嫩滑爽口,真可谓人间美食。我还喜欢素蕨菜沾有水豆豉的辣椒水,嚼起来满口生津,口齿生香。
蕨菜,别看它只是大自然中一种普通的植物,对我们农村人来说它可是个“宝贝”。一年四季,我们都离不开它。春天,我们漫山遍野地抢着采摘嫩蕨菜回家一饱口福;夏天,长成熟了的蕨菜可作牛的吃食;秋天,大人们把“狼鸡叶”割下来,一捆一捆地挑回家放进牛圈里“垫圈”,牛马猪羊每天在上面拉屎撒尿,来来回回地踩踏、揉搓、发酵,等到来年春天,再把它刨出来便是春耕生产不可或缺的肥料了;冬天,天气寒冷,枯黄的“狼鸡叶”成了我们放牛娃烤火取暖的首选,大火一烧,我们围着火堆你追我打,好不热闹。“狼鸡叶”烧成灰,用小木棍把它撵成堆,再用小石头把它圈起来,然后把从家里带来的洋芋、包谷、糍粑往火堆里一扔,几分钟后,一股香喷喷的味道弥漫山间,刺激着我们的味蕾,大家你争我抢变成了大花脸,互相看着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不得不说,这股香甜的美味,弥补了当时我们农村娃娃单调的童年生活。不过,一年四季里,我最喜欢的还是春天里采蕨菜。
每次采摘,我和小伙伴们背着空书包,各自散乱在山坡上,睁着大大的眼睛,慢慢挪动着脚步,轻轻扒开丛林杂草,小心翼翼地仔细寻找,生怕稍不留神漏掉一处。若是发现一处,立刻半蹲,弯下腰,伸出手,一棵挨着一棵地连续采摘,“咔、咔、咔”的声响,脆生生的,像一曲优美的乡间小曲充斥着我们的耳膜,愉悦我们的心情。采完后,用手简单地捋一捋,闻一闻,一股混合着泥土气息的清香味扑鼻而来,让人觉得瞬间舒爽。那时,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,每人独自寻找,谁先找到就是谁的,其他人不许抢,回家时愿不愿意分给别人,自己说了算,但总有调皮捣蛋的孩子违反约定。记得有一次,我先发现了一处,欣喜若狂地跑过去,就像宣布领地一样大声说:这是我发现的。不远处比我高出一个头的小会听见了,三步并作两步迅速跑过来,二话不说,伸手就摘,我一看急了,就冲过去挡在她面前不许她摘。哪知她却朝我大吼一声,又不是你家的,我就要摘,还怒气冲冲地抢了我手上的几棵蕨菜,最后竟然用力把我推开。我一不小心一个趔趄坐到在地上,双手正好落在长满了刺的荆棘丛中,几棵尖尖的大刺立即插入我的手掌,一股钻心的疼,我拿起手一看,鲜红的血液淌满了手心,委屈的泪水忍不住掉下来,咬牙切齿地爬起来就想和她打架。可我矮小的个儿哪是她的对手,还好一旁的小伙伴们赶紧拉开了我们。天渐渐的黑下来,我们赶着牛快进入村口的时候,我气鼓鼓地正盘算着怎样找人一起打她一顿时,小会扭扭捏捏地走到我面前,手捧着一堆鲜嫩的蕨菜,笑嘻嘻地对我说,对不起了,别生气了,这些蕨菜都给你咯!明天我们一起放牛吧!
时光荏苒,光阴似箭。我从初中毕业就到外地求学,毕业后分配到离老家几十公里的乡政府工作、安家落户,十年后才调回清镇小城。远离了老家,远离了儿时的伙伴。惶惶30余载,如今,那个承载着我儿时梦想的老家已全部被拆迁,找不到踪影,但老家的村庄、后面的山坡、儿时的伙伴却经常在我的脑海里不断被修复,不断被重启……
文/郭忠静
视觉/实习生 任梦娟
编辑/彭芳蓉
二审/赵相康
三审/李缨